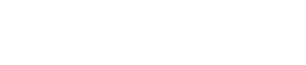《爱情三部曲》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及研究
一、关于小说《爱情三部曲》的创作情况
林吉安(以下简称“林”):鲁老师,非常高兴能跟您谈一谈您的这部小说《爱情三部曲》。之前讀过您的不少文章,但都是学术类的,像这种非学术类的文学作品还是第一次,是一次非常愉快、兴奋的阅读体验。请问这本书是您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吗?
鲁晓鹏(以下简称“鲁”):应该算是。不过,其中第二篇《回北京》以前在石家庄出版的文学杂志《长城》上发表过。①
林:请您谈一谈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和经过吧。
鲁:像我这种在大学里教文学课程的人可能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自己也写一点东西。因为我们老教别人东西,教了一辈子,有时候也想自己尝试一下。但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时间,只是断断续续地、挤出点时间来搞一些文学创作。
由于我是教电影、文学和文化理论的,不是教创作,因而这些东西对我职称评估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浪费好多时间。那完全是一种爱好。我从小就喜欢看文学书籍,有时候也想:为什么自己不能写写呢?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工作了一年,教学任务不是太重,就开始有写作的想法,后来把一些生活体验写在了《回北京》这篇中篇小说里。当时写得很粗糙,写完就放下了,不太满意。很多年后回头整理了一下,发表在《长城》杂志上。后来有一年我作为美国的富布莱特学者去乌克兰基辅工作,在那儿也有一些感受。我当时用英文写了一个很粗糙的中篇小说,就是后来的《西域行》(又名《乌克兰之恋》)。
林:那后来是您自己翻译为中文的吗?
鲁:大部分是自己翻译,有的是重新写的。后来我正好跟中国的出版社接触,于是就决定先把中文版的事情做成,至于英文的稿子怎么弄,看以后的精力和愿望。
三部曲的第一篇《感伤的岁月》是我多年来跟家人谈话,耳濡目染,对家人有了更多了解后写成的。我父亲去世很早,我是从母亲那里得到很多关于家庭的信息。后来我就把故事从头到尾写了一下,也包括我自己经历的事情。之前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片段,直到两年前我有一个休假,大半年时间不用教书,于是就把以前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下,把它们连串到一起,就成了《爱情三部曲》。
林:在小说《回北京》中,以您本人为原型的主人公齐振飞曾说到自己的写作计划:“写我自己熟悉的事情,我见过的、我经历过的事情。写当代的中国和美国,中西之间的文化差异、误解、沟通、认同。”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您创作这三篇小说的共同动机和目的?
鲁:对。这三部小说,尤其是《回北京》和《乌克兰之恋》有一些自传的色彩,但也不完全是自传。我是有意地将虚构和真实进行穿插叙述,同时还故意尝试所谓“元小说”的写法,就是小说里写小说,小说的主人公说“我在写小说”。我故意这样写,因为我看过类似的文学作品,也教学生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文学体验、文学游戏,也算是一种经历,一种实践吧。
林:小说《感伤的岁月》中多处出现大段的“原始材料”,比如姜朴介绍经济发展的文章《西北大省经济建设的开始》,晓妮写给哥哥的诗《寄给远方的哥哥》,还有晓峰的“期末总结”,等等,那种叙述方式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时代气息,这些都是实有其事的吗?能否谈一谈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处理现实与虚构问题的?
鲁:那些材料都是真实的。那首诗《寄给远方的哥哥》确实是我姐姐写给我哥哥的。那个“期末总结”也是我本人几十年前初中还是高中时候写的东西,是我以前翻抽屉时翻到的。这是真实的,我一个字都没改。
林:从内容的表达方式也能看出那个时代的特色,现在很少有这么写的了。
鲁:对。我是故意用了一些原始材料,增加一些真实感。那个《西北大省经济建设的开始》来源于我父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你网上一搜索就能看到。那是一篇真实的文章,我挺喜欢。我就想给我这小说增加一些真实性、历史性。我觉得这也挺好,一方面是半虚构,同时又有些真实的、历史的材料,能把东西写得更丰富一些。但是我也故意以假乱真、以真乱假,就像《红楼梦》开始不是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嘛。还有像唐朝的一些传奇小说,它明明是假的故事,但故意弄得特别真实,作者在小说结尾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国外文学作品里也有类似的,像拉丁美洲的作家博尔赫斯,他经常把假的东西弄得非常真实。这其实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手法,一种文学实践和游戏。
但我还是想通过这些历史材料,给作品注入一些历史深度。我不能像当下一些年轻人那么写东西。我有我的历史记忆,我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我还是想保存一些真实的历史色彩。我写的这个东西没有针对性的大众读者,可能有个小众,这无所谓,我只是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把我的一些真实感受、一些思想,还有我对历史的见证写进去。如果这小说有一些历史维度或历史深度的话,我就很满意了。
林:小说中还经常引用一些富有时代色彩的歌曲,比如陕北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毛泽东时代的红色歌曲《北京颂歌》,以及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等,这些歌曲的使用一方面烘托了时代气氛,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起到了沟通人物情感的作用,这跟电影中的配乐颇有相似之处。而您的整个小说叙事其实也都带有很强烈的电影感,这是否受到电影方面的影响呢?
鲁:可能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吧。我没有特意模仿,但是我一半的工作就是电影教学、电影研究,因此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影响,思维的时候画面先出现。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林:小说《感伤的岁月》中,有一些细节颇具神秘色彩,如开头出现的两个云游和尚,给彭怀玉预测未来,说下一个孩子将“一生坎坷”,会“克母、克夫”,后来果真应验了。又如,陕北老家被描写成一个生育后代的“福地”,姜朴和吴缦华、晓荣和柳娟,都是在这个地方怀上小孩的。这种情节设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吗?
鲁:这种神秘色彩在中外文学里其实挺多的,像我们中国的《红楼梦》就有这个色彩,外国文学作品中也有魔幻现实主义。我觉得渗入一些神秘色彩的东西,可以增加小说的维度。它有些是真实的,是家人跟我讲的。我是有意地从不同方面来烘托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
林:小说《感伤的岁月》开头是1940年代末吴缦华决定放弃出国机会,响应祖国号召,远赴西北参军,而结尾则是1970年代末晓峰在母亲吴縵华的安排下远赴美国留学,体现了两代人在不同时代下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这种时代和人生选择的差异、对比,是主要根据事实情况来记录的呢,还是您有意设计的?
鲁:两方面都有吧。《感伤的岁月》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的家庭或家族方面的一些材料,它有很真实的东西,有些是真实历史发生的故事,但有些事情不能直说。当然,小说要选择叙事角度、叙事方法,有些是经过设计的,小说里事件的发展需要编排。跟一般人来说,我觉得我的经历算是挺丰富的,我走南闯北,见过不少事情;但跟我妈妈那代人来比差远了。她们对一些事情刻骨铭心的体验,她们的历史深度、深沉感和坎坷经历,我还是没法比。我又想起我父亲那一代人经历的事情,他们经受了那么多生死磨难,一刹那间就可能导致死亡或者承受巨大的屈辱,几十年背着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得不到平反昭雪。我个人生活上、学业上、工作上、恋爱婚姻上的一些不顺利,跟他们那一代人完全不一样。
林:小说《回北京》的结尾,当主人公即将离开北京,站在院子里,看到妈妈在练气功时,忽然想起了很多古代文献,如《易经》《天问》等,并直接引用了其中五段,而这跟前面的情节内容似乎没有直接联系,您用在这是想表达什么吗?
鲁:我觉得气功跟宇宙、自然都有联系,因为练气功讲究的是浑圆气。结尾引用这些古诗词主要是想通过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和意识流,让主人公重新回到古代哲学和文学情境中,从而表达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是对宇宙天地、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思考。
林:是不是说他最后在古代文化里面找到了一种认同感?
鲁:可以这么说。但是现代生活的体验同样重要。我也故意把小说写得比较复杂。在小说结尾,我用后记的形式附了一首《忆旧游》诗,意思是说这事还没完,主人公还在追寻,还有其他事情要发生。我故意把这事情弄成好几个层次,主要是想讲述一个华人男性不停地追寻自己的身份,就像屈原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事实上,这个在世界文学上也很普遍,像歌德的《浮士德》不就是讲一个人在不断地追求吗?
林:您的小说时空变化很大,而且经常在不同空间、东方与西方、历史与当下之间穿梭、跳跃,同时主人公也经常处于一种变动不居、浪迹漂泊的生存状态。这种漂泊既是寻找爱情的过程,也是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直到结尾时,主人公终于结婚生子,才结束这种漂泊的生存状态。这种漂泊状态是否是您过去几十年的某种心境写照?
鲁:可以这么说。《爱情三部曲》有个人自传的痕迹,但又不完全是。我后来把这三篇连在一起,是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第一篇小说里,小主人公还在寻找他的未来,他在上中学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到美国后又暗恋另一个女同学,最后都没有结果,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回到北京后,他又在寻找,但都不满意。在生活中我也很长时间处于这种漂泊状态。比如,1999-2006年,七八年间,我每年搬一次家:第一年在宾州匹兹堡市,第二年搬到北京,第三年又回到匹兹堡市,第四年搬到加州萨克拉门托市,第五年搬到加州伯克莱市附近,第六年去了乌克兰,第七年搬到加州戴维斯市,第八年定居在萨克拉门托市。那时我已是不惑之年的人了,真渴望能稳定下来,不再迷惑,不再折腾。三部曲的最后一篇可能给人一种终结的感觉,主人公结婚了,还生有两个孩子,可能是把这个事情画了个句号。这种漂泊是真实境况,也是一种比喻,一种符号,代表我这一代人在海外多年来寻找、打拼的过程。从广义上讲,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不管你在何地,在海外,还是在国内。
林:作为一名比较文学教授,您肯定看过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您觉得哪些作家和作品对您的创作比较有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鲁:没有刻意模仿某个作家,也没有某个具体的作品对我有特别大的影响,可能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我的经历跟任何人都不一样,所以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我可能接受到一些作家的影响,但我不能说某个人的东西就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林:您接下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鲁: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再尝试写一些小说,或是诗歌。但目前我实在没有时间,学术上的应酬太多,忙不过来。我真希望有一天少些应酬,能搞一些文学创作,这是一个愿望。所以这只是开个头,几年以后我有休假了,可能有机会再写一些东西。
二、文学创作与批评
林:您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工作,而现在“转行”搞创作,是否遇到过角色转换的困难?因为毕竟研究和创作有很大区别,研究需要非常理性,而创作可能更多需要感性一些。
鲁:刚开始创作的时候真是非常困难,我像个书呆子,学究气非常重,写的东西也非常学究。现在还有一些人说我的小说有点学究气,像个知识分子小说。是有这个问题,刚开始写时挺累的,也写不好,后来我真正感悟到怎么写小说,开始开窍、入门时,那时已经大半年过去了,又马上要开学,要回去教课了。我相信如果再给我一年时间,我不教书,不写学术文章,我会写得更好。
作为一个学者,有时候需要综合,把事情抽象化,比如说,对文学的发展,对电影的看法,对世界文化的走向,等等,用文章概括下来。它要总结和抽象,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从特殊到普遍。而写小说是个完全相反的过程。在写小说时,你不能直说你的思想,不能讲大道理,你要通过人物、细节来讲。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有时候我转变得不太好,可能有时候主人公跳出来自己说话,这就不太对。我也在摸索。而且,在我的小说里,主人公的东西太多了,而其他人物比较弱,因为我老想写我个人的经历,捕捉其他人就稍微少了一点。如果有机会,我可能会更多地捕捉一些其他人的东西。但是这也不一定,有的作家,像郁达夫,写自己的事情,主观的感受多些,那也可以。他不是茅盾,茅盾要写很多人物,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所谓客观的写法。鲁迅也写一些其他的人物。我觉得这两种写法都可以。如果有时间,我也可以换一种客观的写法,多写其他人物,不要老写基于男主人公的个人经历。
林:在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平衡批评与创作的关系的?您作为一个学者,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创作过程中跳出来分析自己的作品?
鲁:可能会有,因为我是教文学、电影的,可能有一些高屋建瓴的概念在不自主地指导我的写作,因为我的写作是有意识的,可能有些东西不是特别自然。可能有一些先行的、指导性的东西。一个是批评家,一个是创作家,这两个角色有时候混淆了。最好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但我肯定做不到,因为我几十年来都是搞文学理论教学工作的,所以有时候角色转换还不太到位,还要继续地磨合。
林:从历史上看,其实很多作家都是创作和批评研究兼具的,比如鲁迅、郭沫若、钱锺书等,只是有些作家更偏向研究,是学者型的,而有些作家则纯粹搞创作,是职业型的。您觉得哪种状态更容易出优秀作品?
鲁:这个很难说。有时候我挺羡慕那些职业作家,他们有时间,可以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但是他们靠这个生活,要赚钱,有时候又得写一些迎合市场需求的东西。所以每个职业都有它的长处和遗憾的地方。我也看到过一些报道,有些作家年纪轻轻的就赚了很多钱,会取悦读者,但是他们也希望有一天写一些自己真实的东西。我有时候也想,我为什么不能做职业作家呢?天天写东西不就完了嘛?但我的职业不是这个,写小说只是业余的。如果能挤出时间来写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也还可以。我不会因为要产生轰动效果,不会为了赚钱,或者是商业运作而去写,我就写我想写的东西。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虽然是两袖清风的读书人,但起码衣食无忧,因此也不需要为追求商业效果而写东西。我可以把我的思考写在小说里,这就可以了。
林:从学术研究和批评的角度来看,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自己作品的?在三部曲中,哪篇小说您最满意?为什么?
鲁:这三部中篇小说写出来以后,我偶尔也跟个别人聊一下,有些同事或同学觉得《感伤的岁月》给他们印象最深,觉得它有一些历史深度。这三篇我本人都喜欢,都是我真实感受的表达。《感伤的岁月》那篇小说写得短了一点,没有充分展开,有点遗憾。如果能展开的话,真可以显示出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以及人们经历的悲欢离合。这个故事的素材本身可以写成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里边可以有上百个人物。如果给我一年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可以写下来,但现在就只能这样了。但如果以后有人愿意把它改编成电视剧的话,那还可以丰富展开。但就目前来说,我也比较满意,因为它表达了我这一代人对社会、对中国历史、对世界历史的一些认识。我想写一些关于中国历史的东西,给大家展示出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人物经历的悲欢离合、历史沧桑。小说里的一些人物经历了很多,比如,男主人公的父亲经历的一些政治运动,里头有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也不能直说,因为人家都有后代,我也不能逞一时之快而伤及无辜。另外,对于一般人读那篇小说时,我也会给他们介绍一篇我妈妈的口述历史,回忆她的老师。林缦华口述,鲁晓鹏、程园整理:《大变革时代的求学经历:回忆恩师吴玉如、容庚、陈寅恪、龙榆生先生》,《文汇学人》2015年8月28日。她当时在岭南大学念书,那是真实的故事。小说有虚构的成分。如果将真实的历史和半虚构的小说进行对比阅读的话,大家会对历史的各个层面有更全面的了解。
《回北京》读起来可能比较肤浅,但我是故意这样写的,就是通过一个男人的性爱来写他的身份认同。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文学正好出现了所谓的美女作家。美女作家的写法就是暴露、虚构很多性爱经验。她们有意这么做,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短暂风尚。后来又有所谓的美男作家,如上海大学的葛红兵,他在小说《沙床》中也在夸张、虚构一个男主人公各种各样的性爱经历。我也可能稍微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我写这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个人体验,但事件发生的顺序可能会重新安排一下,比如说不同年份发生的事情,我把它弄在一年里,或者我发生的事情安排到别人身上,但大概是有些生活来源、生活经历的。我想通过爱情来讲述一个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当他回到中国后,他面临着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的问题。
我到达乌克兰后也有一些思考。我思考社会主义的现状、命运,俄罗斯的问题,乌克兰的问题,以及中国几代人的社会主义情结。我觉得这在《乌克兰之恋》这篇小说里也得到了一些体现。乌克兰原来是苏联的一部分,后来独立了,于是就出现了乌克兰人跟社会主义的关系,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等复杂问题。小说主人公是作为一个美国派到那的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同时又有社会主义中国的背景。他面临着一些困境,一方面美国鼓励他支持橙色革命,去俄罗斯化;但另一方面当他碰到当地的俄罗斯裔人后,发现他们愿意跟随俄罗斯,因为他们有血缘关系,他们的父母就是俄罗斯人,他们原来是苏联人,他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乌克兰人。我当时作为一个旅行者、观察者,也对这些身份认同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命运有了一些直观的认识。
在《回北京》和《乌克兰之恋》这两篇小说里,爱情是表面的,主要是想通过爱情来讲一些更深的东西。在小说中,你不能枯燥地讲大道理,那没人看。如果你通过爱情来讲,大家可能就更喜欢看一些。比如,主人公先认识一个乌克兰姑娘,通过她了解到乌克兰人的想法,后来又认识了一个俄罗斯裔的姑娘,他又接触到俄罗斯人的境况。同时他又是中国男性,在美国工作,于是又把他的社会主义背景和家庭背景都揉进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处理来表达几代人对全球社会主义发展的思考和反思,可能更有意思。
三、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
林:您作为美籍华人,您的小说创作自然也可归属到所谓的“海外华文文学”的范畴当中,而您又长期从事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那么,能否请您谈一谈“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情况,如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鲁:“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个范围越来越大,现在研究這方面的人也越来越多,像中国就不少大学、机构专门研究海外华文文学。
“海外华文文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很难定义。早期的比如说古代的越南、日本、朝鲜,很多人用汉语写作。在越南,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宫廷使用的语言文字就是汉语。但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那时候有帝国,有蕃属国,还有中华文化圈,等等。所以从广义上来讲,在周边海外国家用汉语写作的时间就太长了。咱们就从近代开始讲吧。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去日本、美国留学,在海外写作。比如说,廖仲恺的兄长廖恩焘,还有像梁启超这些人,他们就曾用中文在日本写作,他们可以算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先驱。另外,郁达夫、郭沫若他们也都曾在日本留学,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写的,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也都在日本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外华文文学”那时候就已经有了。
“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只是想强调一点,据我了解,近年来海外华人女性作家特别多,男性作家相对少些,有名的、大家讨论比较多的都是女性作家。可能这跟她们的职业有关,因为男性往往选择工程、计算机、法律这类比较实用的专业,他们很少从事写作。而有些女性则愿意从事这方面工作,所以海外华人女性作家比较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以及虹影的一些作品,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人。而男性作家则比较少,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后来这个小说还被拍成电视剧,姜文主演,在中国产生很大轰动。相对来说,华人女性作家对婚姻、性爱、主体的构建等方面挖掘得比较多。她们的小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女主人公碰见各种男人,其中有中国的前夫或华裔男性,还有异族男人,于是产生困惑、抉择。女性作家比较大胆,她们通过婚姻、性爱,以及中西文化差异,来展示出她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男性作家少一些。曹桂林在《北京人在纽约》里面开始剖析一些男性的问题,但这方面的作品不多。所以我希望能看到有更多的华人男性作家大胆地从他们的角度来挖掘、描写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我想看到更多的小说讲男人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的问题。
整个世界,女性作家越来越多,因为男人需要“务实”、赚钱。我当年想要学比较文学,家里人都不同意,说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也完全理解家人的这种担忧。我希望有更多的男性作家来剖析男性所经历的跨文化窘境,剖析他们的主体性建构。这是我对海外华人作家的一点期待。
林:正如前面所说,您创作小说的动机主要是想探讨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误解、沟通和认同,而这些似乎也是很多海外华文文学反复探讨的主题。在这方面,除了海外作家对中西方文化均比较了解这一优势外,是否与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也有关,进而使其作品区别于大陆本土的华文文学?
鲁:对,是这样的。正像你所说的,由于海外华人的独特生命体验,身份认同问题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这是由他们的经验所决定的。当然,这种身份困惑问题也是相对而言,中国文学也有探讨这方面的,只是海外华人的感受更强烈,而且是必须要走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原先是中国人,突然一下成为其他国家的移民,而且要用人家的语言说话,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这个小说讲的就是关于身份认同的追寻与模糊,比如小说《回北京》里,男主人公突然收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居留证”,他当时都震惊了。他是回家啊,他是在北京长大的,怎么还要居留证,还要到派出所报到、注册?虽然这类人已经入美国籍,被“归化”了,但是猛然间还是有些震撼。
林: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请您介绍一下国外学术界关于“华文文学”的研究情况。
鲁:在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比较新。就拿美国学界来说吧。有广义的“中国文学”研究,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很大的机制,有几十年的历史,可以算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分。另外又有Asian American Studies(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那是研究用英文写的作品,是美国研究(“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的一部分,是研究在美国的亚裔文学。我们这个“海外华文文学”,不中不西,不左不右,夹在中间,是在美国的华人用中文写的东西。“世界华文文学”或者“海外华文文学”的归类就很有意思。现在又有人推出一个新词,叫做“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就是说,凡是用中文写的作品都可以算是“华语语系文学”。
在世界任何地区用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算成华文文学。历史上,海外华文文学最大、最集中的板块是南洋,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那里居住着千百万的华人。很多华侨从小就说华语(汉语)。在新加坡,华语是官方语言之一。在中国,人们讲“汉语”;在南洋,人们用“华语”。“华语电影”这个说法就是起源于南洋。
20世纪初,廖恩焘、梁启超、郭沫若、郁达夫等大量中国人在日本用中文写作。你不能说这是日本文学,因为那些人很快就回到中国,而且那时候没有“离散”(diaspora)的研究范畴,他们也不能加入日本国籍。所以这类作品可以算是中国文学,当然也一定是广义的中国文学。但到我们这个年代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跨区域、跨国、全球化的语境下,原来那种传统的民族文学的概念可能就不太适用。就像电影一样,比如《卧虎藏龙》是哥伦比亚公司出品,但又由李安导演,还有中国的公司参与,这种跨国生产、跨国制作现在已经很普遍了。所以我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算作是中国文学,我很荣幸,很光荣。说它是华文文学,应该是没问题的。说它是华语语系文学,也可以。
林:请您介绍一下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吧。您刚才也说到林语堂先生他曾用英文写过《吾土吾民》,这本书似乎在海外的影响较大,这可能跟他采用英文写作有关。但绝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是用中文写作的,他们的作品接受情况如何呢?
鲁:林语堂写《吾土吾民》的时候,那是20世纪上半叶,当时大部分人是没有林语堂那种能去国外并用英文给西方主流读者写东西的条件,也没那水平。林语堂有他特殊的历史机遇,他写的《吾土吾民》介绍中国的哲学、饮食等等,在国外确实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中國国内就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因为它那个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对国人来说,深度不够,也没新意。
海外华文作家的读者群其实很有限,他们没有相应的发行渠道,这个可能是海外作家的困境吧,起码在北美,情况如此。比如说我写这本书,如果在中国,可能同事、同学、学生、单位就给我搞个新书发布会,介绍一下,或是书店搞个活动,同人之间互相介绍一下,但这些在美国做不到。不过,正如司马迁所说的,他写的《史记》可以“藏之名山”。一百年以后,如果有个人突然翻到我写的这个东西觉得挺有意思的话,那我就满足了。
【作者简介】鲁晓鹏(Sheldon Lu),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林吉安,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桂玲)